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lǐng)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lǐng)未來
醫(yī)脈通導讀必須指出,對于選擇抗抑郁藥而言,一些很有潛力的精準醫(yī)學手段,如遺傳學、神經(jīng)影像學、行為及認知標志物等,現(xiàn)階段臨床應用價值仍相當有限。相比而言,本文作者更建議首先基于抑郁亞型及癥狀群選擇抗抑郁藥;若效果不佳,再基于癥狀嚴重度選藥。針
醫(yī)脈通導讀
必須指出,對于選擇抗抑郁藥而言,一些很有潛力的精準醫(yī)學手段,如遺傳學、神經(jīng)影像學、行為及認知標志物等,現(xiàn)階段臨床應用價值仍相當有限。
相比而言,本文作者更建議首先基于抑郁亞型及癥狀群選擇抗抑郁藥;若效果不佳,再基于癥狀嚴重度選藥。針對同一類抗抑郁藥,可根據(jù)患者的人格類型、患者個人喜好、軀體/精神科共病及副作用具體加以選擇。

抗抑郁藥(AD)的選擇同時受到醫(yī)生個人、患者、疾病特征、藥物自身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事實上在此之前,針對一名具體患者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藥物治療是否優(yōu)于非藥物治療:
▲ 對于原發(fā)性的生物因素突出的抑郁亞型,軀體治療的效果往往優(yōu)于非軀體治療。例如,針對精神病性抑郁,電休克治療(ECT)及抗抑郁藥聯(lián)用抗精神病藥的療效較好,而心理治療并非推薦治療手段。再例如,針對憂郁型(melancholic)抑郁,ECT及抗抑郁藥的療效優(yōu)于認知行為治療。
▲ 對于非憂郁型抑郁,抗抑郁藥的總體療效有可能不及心理治療,但仍可以為患者帶來一定的獲益,包括緩解共病焦慮;某些關(guān)鍵的素因,如病前適應不良的人格因素,應被視為心理治療的焦點。
▲ 對于一過性抑郁或類似狀態(tài),抗抑郁藥不應成為初始治療選擇:此類患者的安慰劑效應顯著,且自愈比例很高,一些初級的心理干預已經(jīng)足夠,而用藥可能弊大于利。
另一方面,僅僅根據(jù)抑郁癥狀嚴重度選擇治療方案,如針對重度患者使用ECT,針對中度患者使用抗抑郁藥,針對輕度患者使用心理治療,同樣存在過度簡化之嫌。
一項12月23日在線發(fā)表于Acta Psychiatr Scand. 的綜述中,來自澳大利亞的研究者通過回顧相關(guān)文獻資料,對臨床選擇抗抑郁藥時需要考慮的因素進行了詳細論述。以下為主要內(nèi)容:
一、抗抑郁藥因素
1. 療效/有效性
就抗抑郁藥大類而言,針對老藥(如TCA)及新藥(如SSRI)的總體療效孰優(yōu)孰劣,目前證據(jù)不多且并不一致。有觀點認為,根據(jù)早期研究結(jié)果所得出的「老藥療效優(yōu)于新藥」的結(jié)論值得商榷,可能與近年來安慰劑效應的增強有關(guān)。
然而,具體到憂郁型抑郁,證據(jù)則相對明朗:TCA優(yōu)于SSRI,SNRI也略優(yōu)于SSRI。
就具體抗抑郁藥而言,2018年的一項大型網(wǎng)絡meta分析顯示,相比于安慰劑,阿米替林治療有效的OR值最高(2.13),瑞波西汀最低(1.37);不同抗抑郁藥相比時的OR值為1.15-1.55。頭對頭比較中,阿戈美拉汀、阿米替林、艾司西酞普蘭、米氮平、帕羅西汀、文拉法辛及伏硫西汀較其他抗抑郁藥更有效(1.19-1.96),而氟西汀、氟伏沙明、瑞波西汀及曲唑酮的療效最弱(0.51-0.84)。
盡管該研究的方法學較為嚴謹,但此種定量手段手段仍可能受到抑郁癥異質(zhì)性及入組問題的影響,故僅供臨床參考,而并非金科玉律。
2. 副作用/耐受性/可接受度
有研究者分析了SSRI、SNRI、米氮平、曲唑酮及萘法唑酮的不良事件發(fā)生率,結(jié)果顯示總體發(fā)生率相仿,但具體不良事件上存在差異。SSRI與其他第二代抗抑郁藥的不良反應停藥率類似,但度洛西汀及文拉法辛的停藥率分別較SSRIs高67%和40%。總體而言,新藥的副作用可能少于老藥,也可能并不比老藥少,而副作用的類型和模式與老藥存在差異。
同樣是上述網(wǎng)絡meta分析,相比于安慰劑,阿戈美拉汀的可接受度(全因停藥率)最理想(OR 0.84),而氯米帕明最差(1.3)。頭對頭比較中,阿戈美拉汀、西酞普蘭、艾司西酞普蘭、氟西汀、舍曲林及伏硫西汀的可接受度高于其他抗抑郁藥(0.43-0.77),而阿米替林、氯米帕明、度洛西汀、氟伏沙明、瑞波西汀、曲唑酮及文拉法辛的停藥率最高(1.30-2.32)。同樣,上述結(jié)果僅供臨床參考。
3. 藥代/藥效動力學
傳統(tǒng)抗抑郁藥的分類多基于其化學結(jié)構(gòu)(如「三環(huán)類」),而新型抗抑郁藥的分類主要基于其作用機制(MOA)。不同藥物針對具體神經(jīng)遞質(zhì)轉(zhuǎn)運體和/或受體的效應也存在差異。例如,西酞普蘭對5-HT再攝取的抑制作用強于NE,而去甲替林相反。然而,這種機制上的差異尚不能客觀準確地外推至臨床,不宜過度演繹。
起效速度對于選擇抗抑郁藥具有重要意義。若抑郁存在某些危險特征,如自殺傾向,某些抗抑郁藥(如米氮平)的起效速度快于SSRI,或可優(yōu)先考慮。一些機制不同的新型藥物(如氯胺酮)可在數(shù)小時內(nèi)起效。
4. 藥物相互作用
選擇抗抑郁藥時,聯(lián)用藥物及潛在藥物相互作用需要考慮。例如,若患者同時使用鈣通道阻滯劑,聯(lián)用TCA前則應考慮到QTc間期延長的風險。使用所有抑制5-HT再攝取的抗抑郁藥均可升高出血風險,尤其是聯(lián)用阿司匹林及非甾體抗炎藥時。一些SSRI可抑制CYP2D6,進而升高某些藥物的血藥濃度。作用機制類似的藥物可能產(chǎn)生協(xié)同效應,如TCA的抗組胺能效應可強化酒精的鎮(zhèn)靜效應,升高呼吸停止的風險。
5. 治療費用及藥品質(zhì)量
選擇抗抑郁藥時應考慮到治療費用問題。盡管某些仿制藥可能存在質(zhì)控方面的問題,但仿制藥總體上具有價格優(yōu)勢。
6. 證據(jù)強度
抗抑郁藥的證據(jù)強度同樣具有參考價值。有研究者定量分析了16種第二代抗抑郁藥的證據(jù)強度,絕大部分藥物均具有很強的療效證據(jù),但程度上存在差異:匯總后效應量最高的是文拉法辛,其次為帕羅西汀;效應量最低的是安非他酮和維拉唑酮。
二、疾病因素
1. 嚴重度
對于中重度抑郁,三/四環(huán)類抗抑郁藥的治療有效率為50%-75%,安慰劑為25%-33%。對于相對較輕的抑郁,抗抑郁藥與安慰劑的療效差異較小。很多抑郁癥方面的meta分析顯示,之所以出現(xiàn)上述現(xiàn)象,原因可能在于非常嚴重的抑郁患者對安慰劑的反應更差,而并非在于藥物對這些患者療效更好。然而,抑郁越嚴重,存在憂郁特征的可能性也越大。
針對較重的抑郁,指南的意見較為一致:應優(yōu)先選擇藥物治療或ECT,而非心理治療。然而,在嚴重度較輕的一端,指南的意見并不一致,包括建議用藥,建議「觀察性等待」,以及建議將心理治療作為一線治療手段。
對于輕中度抑郁,大部分抗抑郁藥的療效似乎相當。抑郁更重時,抗抑郁藥的差異逐漸顯現(xiàn)出來,艾司西酞普蘭的臨床治愈率高于氟西汀、舍曲林、帕羅西汀及西酞普蘭。有報道稱,針對住院抑郁患者(其中很多人存在憂郁特征),氯米帕明的療效優(yōu)于西酞普蘭、帕羅西汀及嗎氯貝胺。總體而言,抑郁越嚴重,越適合使用抗抑郁藥,一些證據(jù)顯示作用機制更「廣譜」的藥物療效更佳。
2. 抑郁亞型
(1)憂郁型抑郁:相比于其他抑郁亞型,憂郁型抑郁具有更明確的軀體表現(xiàn)(如精神運動性紊亂)及較強的生物學基礎(chǔ)。針對這一亞型,抗抑郁藥的療效優(yōu)于心理治療(如認知行為治療)。大量研究顯示,TCA針對這一患者群體的療效優(yōu)于SSRI,治療有效率分別為57%和18%。對于存在憂郁特征的住院抑郁患者,兩項研究均顯示文拉法辛的療效優(yōu)于氟西汀;另有研究顯示,TCA療效優(yōu)于MAOI。
一種觀點是,作用機制更廣的抗抑郁藥可作用于NE及DA系統(tǒng),而這兩個系統(tǒng)與憂郁型抑郁患者的精神運動性紊亂相關(guān),進而療效更好。
(2)伴精神病性癥狀的抑郁:有研究者對各類藥物的療效進行了定量分析,發(fā)現(xiàn)抗精神病藥單藥治療針對「妄想性」抑郁的有效率為19%,抗抑郁藥單藥治療的有效率為41%,兩者聯(lián)用時有效率為78%。兩項Cochrane薈萃分析均顯示,抗抑郁藥聯(lián)用抗精神病藥針對精神病性抑郁的療效優(yōu)于單用其中一種,且TCA的療效優(yōu)于新型抗抑郁藥。
(3)非典型抑郁:非典型抑郁的特征通常包括睡眠過多、食欲亢進、心境反應性、灌鉛樣麻痹等。針對此類患者,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長期被視為有效的治療手段;有meta分析顯示,此類藥物針對非典型抑郁的療效優(yōu)于TCA,但也有研究發(fā)現(xiàn)MAOI相比于SSRI的優(yōu)勢可忽略不計。認知行為治療的效果與MAOI類藥物苯乙肼相當。針對SSRI與TCA的相對療效,現(xiàn)有證據(jù)并不一致。
鑒于心理治療與抗抑郁藥療效相當,抗抑郁藥可以作為二線選擇,在心理治療失敗后使用;SSRIs的療效可能與MAOI相差不大,且耐受性及安全性更好。
(4)焦慮性抑郁:通常指高特質(zhì)焦慮個體在非憂郁型背景下的抑郁,與帶有激越特征的憂郁型抑郁存在差異。針對焦慮性抑郁,現(xiàn)有證據(jù)并不確切,很多研究得到了陰性結(jié)果,如舍曲林與丙米嗪無顯著差異,艾司西酞普蘭與去甲替林的有效率同樣相當。然而,一項納入了10項研究的匯總分析顯示,SSRI針對焦慮性抑郁的療效優(yōu)于安非他酮。
3. 神經(jīng)遞質(zhì)
現(xiàn)有抗抑郁藥的一個共同點在于均可作用于單胺能系統(tǒng),但具體存在差異。從理論角度出發(fā),遞質(zhì)系統(tǒng)與某些抑郁亞型有關(guān),進而有助于指導抗抑郁藥的選擇。
例如,針對非憂郁型抑郁,SSRI可有效改善心境癥狀;針對憂郁型抑郁,作用機制更廣的抗抑郁藥有助于覆蓋更多癥狀;針對伴精神病性癥狀的抑郁,聯(lián)用抗精神病藥有助于改善更高水平的多巴胺能紊亂。盡管上述模型的合理性在某些證據(jù)中得到了部分證明,但仍有待更全面的評估。
4. 癥狀群
有研究者認為,與抑郁相關(guān)的主要癥狀群,包括焦慮、疲乏、失眠等,均由一個或多個單胺能神經(jīng)通路調(diào)節(jié):
(1)焦慮、易哭泣及強迫癥狀群:被視為「5-HT能缺陷系統(tǒng)」的一部分。作用于5-HT能系統(tǒng)的SSRI可能優(yōu)于NE能藥物——后者的激活效應可能過強。
(2)疲乏癥狀群:由邊緣皮質(zhì)及藍斑NE通路調(diào)節(jié)。針對存在顯著疲乏癥狀的抑郁患者,可優(yōu)先考慮SNRI(如文拉法辛)或NDRI(如安非他酮),不宜選擇具有鎮(zhèn)靜效果的NaSSA或SARI。
(3)失眠癥狀群:與腦干睡眠中心及5-HT2A受體有關(guān),阻斷該受體的藥物可優(yōu)先考慮,如NaSSA(如米氮平)或SARI(如曲唑酮),或使用具有鎮(zhèn)靜效應的抗抑郁藥(如TCA),不宜使用具有激活效應的SNRI或NDRI。
另有研究者基于數(shù)據(jù)驅(qū)動將抑郁分為三個癥狀群:睡眠癥狀群(如失眠)、核心情緒癥狀群(如易疲乏、心境低落、快感缺乏)及「非典型」癥狀群。針對不同癥狀群,常用抗抑郁藥的療效存在差異。例如,高劑量度洛西汀治療核心情緒癥狀及非典型癥狀的療效優(yōu)于艾司西酞普蘭。抑郁癥狀群也有助于指導抗抑郁藥的選擇,尤其是當患者難以被準確劃入某種亞型時。
三、患者因素
1. 年齡
一項meta分析顯示,對于18歲以下個體,只有氟西汀的療效顯著優(yōu)于安慰劑,而文拉法辛與自殺風險的升高相關(guān)。對于年齡較大的患者,NE能藥物與5-HT能藥物療效孰優(yōu)孰劣,目前尚存爭議;有研究顯示,兩者療效相當。TCA相關(guān)抗膽堿能不良事件(如認知損害)及SSRI相關(guān)低鈉血癥更多見于老年患者。
2. 性別
大量研究未能發(fā)現(xiàn)男女患者對抗抑郁藥反應的差異。有研究顯示,相比于男性,絕經(jīng)前女性對SSRI反應更好,可能與雌激素和5-HT的相互作用有關(guān)。此外,女性似乎更容易對MAOIs產(chǎn)生反應,而男性更容易對TCA治療產(chǎn)生反應,但上述差異在絕經(jīng)后即消失。
3. 圍產(chǎn)期人群
宮內(nèi)暴露于抗抑郁藥可能影響新生兒,如SSRI與新生兒持續(xù)性肺動脈高壓風險的升高相關(guān)。SSRI中,帕羅西汀導致先天性畸形的風險最高。若產(chǎn)前暴露于SSRI或SNRI,新生兒常發(fā)生一過性的停藥綜合征。對于哺乳期女性而言,舍曲林相對較安全,因該藥較少通過乳汁分泌。MAOI與高血壓風險的升高相關(guān),妊娠期禁用。針對圍產(chǎn)期患者選擇抗抑郁藥時,建議閱讀相關(guān)文獻,權(quán)衡利弊。
4. 患者個人喜好
選藥時,考慮患者個人喜好非常重要,有助于改善依從性,以及盡早獲得病情的改善。然而在此之前,應就藥物特點開展宣教,而非完全基于患者自己的理解。
5. 既往治療依從性
抗抑郁藥(尤其是某些SSRI及SNRI)在停藥或減量時可發(fā)生停藥綜合征,半衰期較長的藥物(如氟西汀)風險較低。對于經(jīng)常不依從而自行停藥的患者,提前選擇長半衰期的藥物或許對患者有利。
6. 既往治療反應
如果患者既往對某種抗抑郁藥產(chǎn)生了反應,且耐受性良好,那么再次使用該藥似乎是合理的。然而,這一點仍缺乏前瞻性研究加以確認。
7. 人格類型
基于現(xiàn)有證據(jù),神經(jīng)質(zhì)、人格障礙及氣質(zhì)類型似乎并非SSRI治療的強預測因素。然而,也有研究顯示,對于存在顯著的情緒失調(diào),如終日焦慮擔心,或容易在焦慮基礎(chǔ)上出現(xiàn)易激惹的患者,SSRI可能有用。當抑郁患者共病人格障礙時,TCA的治療轉(zhuǎn)歸并不一致。
8. 過量風險
SSRI過量中毒致死的風險極低,SNRI的風險稍高,TCA和MAOI的風險更高。對于容易發(fā)生自傷的沖動患者,最好避免使用TCA和文拉法辛,或限制患者所能獲取的藥物數(shù)量。
9. 遺傳學
既往研究探討了遺傳學及表觀遺傳學對抗抑郁藥治療應答的影響。例如,STAR*D研究顯示,包括FKBP5、GRIK4、HTR2A在內(nèi)的單核苷酸多態(tài)性(SNPs)與西酞普蘭治療反應有關(guān)。ABCB1基因編碼P-糖蛋白,而后者可限制某些特定抗抑郁藥進入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發(fā)揮作用,因此該基因也與抗抑郁藥的療效及不良反應有關(guān)。研究顯示,就艾司西酞普蘭、舍曲林及文拉法辛(均為P-糖蛋白底物)而言,功能性SNP rs10245483純合子個體使用艾司西酞普蘭和舍曲林時的治愈率較高且副作用更少,而最小等位基因純合子個體使用文拉法辛時的治愈率更高且副作用更少。
其他此類研究有望在不遠的將來助力抗抑郁藥的選擇,但目前臨床價值仍有限。
10. 家族史
若既往有家人對某種抗抑郁藥反應良好,考慮到共同的遺傳因素,患者也可考慮使用該藥。然而,與患者個人抗抑郁藥治療史類似,這一觀點尚停留在理論推演及臨床經(jīng)驗的層面,缺乏支持性的研究證據(jù)。
11. 發(fā)育因素
相比于既往未遭受過虐待的個體,有虐待史的患者對抗抑郁藥物治療的反應較差。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虐待尤其是發(fā)生在7歲之前者可預測舍曲林、文拉法辛及艾司西酞普蘭8周治療效果不佳,而發(fā)生在4-7歲時的虐待更具預測意義:相比于艾司西酞普蘭及文拉法辛,患者使用舍曲林時的治療轉(zhuǎn)歸尤差。有觀點認為,舍曲林對多巴胺能的抑制作用較強,而這一亞組的患者本身即存在多巴胺能紊亂,進而造成了上述現(xiàn)象。
另有研究顯示,相比于抗抑郁藥,有童年期創(chuàng)傷史的患者對心理治療反應更佳。雖然證據(jù)仍有限,但如果個體有創(chuàng)傷史,或許即提示病因中的社會因素較生物因素更突出;此時抗抑郁藥療效可能有限,而應優(yōu)先考慮采用心理治療。
12. 行為及認知因素
神經(jīng)心理測試總體表現(xiàn)較差可預測SSRI治療反應不佳,其中工作記憶缺陷的預測效力最強。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認知功能受損的一組抑郁患者對艾司西酞普蘭的反應更差,但對文拉法辛及舍曲林的反應不受影響。一項系統(tǒng)綜述顯示,SSRIs、安非他酮、度洛西汀、嗎氯貝胺及噻奈普汀可改善某些認知域,包括學習、記憶及執(zhí)行功能等,但證據(jù)質(zhì)量較低。另一項meta分析則發(fā)現(xiàn),伏硫西汀對執(zhí)行控制、處理速度及認知控制的改善效應最突出,而度洛西汀對延遲回憶的改善效應最明顯。
精神運動性遲緩(憂郁型抑郁的核心表現(xiàn))是SSRI治療無反應的預測因素。例如,精神運動性遲緩是氟西汀治療12周后無反應的最強預測因素,而對于使用安非他酮緩釋劑型治療的門診抑郁癥患者而言,治療前精神運動速度慢可預測8周后效果更佳。
13. 神經(jīng)生理學及神經(jīng)影像學
神經(jīng)生理學及神經(jīng)影像學也有望指導抗抑郁藥的選擇。例如,治療前杏仁體對閾下悲傷面容的反應性可預測抑郁患者對文拉法辛緩釋劑型的應答。然而與遺傳學類似,目前臨床應用價值有限。
14. 內(nèi)分泌研究
地塞米松抑制試驗(DST)可測定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異常。一項meta分析顯示,相比于無精神病性癥狀的個體,伴精神病性癥狀抑郁患者的皮質(zhì)醇非抑制(non-suppression)現(xiàn)象更常見(64% vs. 41%)。相比于DST正常的個體,反應異常者對安慰劑的反應更差,且對NE能抗抑郁藥的反應更佳,而前者對5-HT能抗抑郁藥的反應更佳。
15. 軀體共病
SSRIs可能與骨折風險升高相關(guān),針對骨質(zhì)疏松患者使用此類藥物應謹慎。針對肝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可根據(jù)抗抑郁藥的代謝通路加以選擇。肥胖可能影響抗抑郁藥的選擇——相比于安慰劑,肥胖及非肥胖女性均可從SSRI治療中獲益,而肥胖男性使用SSRI和安慰劑的癥狀改善無顯著差異。此外,肥胖的抑郁癥患者使用
文拉法辛緩釋劑型的療效
似乎優(yōu)于艾司西酞普蘭。TCA可升高閉角型青光眼患者的眼內(nèi)壓。
事實上,很多軀體狀況可預測患者對SSRI治療反應不佳,包括高膽固醇血癥、血管性疾病高危因素、低葉酸血癥、白質(zhì)高信號等。
16. 精神科共病
若抑郁患者共病焦慮障礙,則應考慮可同時改善焦慮的抗抑郁藥。例如,針對強迫癥,可考慮使用SSRI或氯米帕明。共病神經(jīng)性貪食可考慮SSRI,而共病神經(jīng)性厭食可使用增重效應較強的抗抑郁藥。發(fā)生于抑郁背景下的物質(zhì)使用障礙可能影響抗抑郁藥的選擇;例如,若患者希望戒煙,安非他酮可優(yōu)先考慮——該藥可降低個體對尼古丁的渴求。
四、治療失敗時
初始抗抑郁藥治療后,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可獲得臨床治愈。若患者反應不佳,且依從性確認良好,可首先考慮增加抗抑郁藥劑量;例如,艾司西酞普蘭(而不包括其他SSRI)、文拉法辛及TCA均呈現(xiàn)量效關(guān)系。臨床中可測定TCA血藥濃度,確定其是否落在治療窗內(nèi),但不推薦測定第二代抗抑郁藥的血藥濃度,因為此類藥物的血藥濃度與臨床反應的關(guān)聯(lián)度較差。
藥物代謝的個體差異可部分解釋抗抑郁藥療效的差異。細胞色素P450酶系(如CYP2D6、CYP2C19)活性的差異很大,從慢代謝到超快代謝,后者可能需要更高的抗抑郁藥劑量。患者的種族也可能有影響,例如只有1%-6%的白人及非裔美國人是CYP2C19慢代謝者,而這一比例在亞洲人中為13%-23%。藥物遺傳學對選擇抗抑郁藥的影響有待大規(guī)模隨機對照研究的確認。
若患者因不能耐受而更換抗抑郁藥,STAR*D研究發(fā)現(xiàn),由第一種SSRI換用第二種時,之前的不耐受并不能預測未來的不耐受。如果因為未能獲得臨床治愈而換藥,換用同類及另一類抗抑郁藥的療效無顯著差異,但憂郁型抑郁可能是個例外。就meta分析結(jié)果而言,如果某種SSRI(如帕羅西汀)治療反應不佳,換用艾司西酞普蘭可能有幫助。同理,如果換用其他類別的抗抑郁藥,也可以參考上文meta分析中更有效的抗抑郁藥。
文獻索引:Bayes A, Parker G. How to choose an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Acta Psychiatr Scand. 2018 Dec 23. doi: 10.1111/acps.13001. [Epub ahead of pr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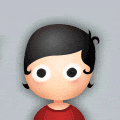
丁楠東
版權(quán)所有 未經(jīng)許可不得轉(zhuǎn)載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備案號:遼ICP備14006349號
網(wǎng)站介紹 商務合作 免責聲明 - html - txt - xml